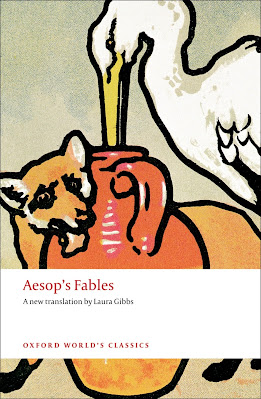剛讀了美國作家Joyce Carol Oates的短篇小說"The (Other) You",聯想到維根斯坦的臨終遺言。
先說維根斯坦的臨終遺言。根據Norman Malcolm的Ludwig Wittgenstein: A Memoir,維根斯坦晚年被診斷患癌後,搬到醫生Dr. Bevan家裏住,方便治療和照顧。他去世那天晚上,陪伴他的是Mrs. Bevan;他臨終前對 Mrs. Bevan 說:「告訴他們,我過了美妙的一生!」("Tell them I've had a wonderful life!")
關於維根斯坦這句遺言,Malcolm 寫了以下感想:
他說的「他們」,無疑是指要好的朋友。當我想到他深沉的悲觀看法、精神與道德上的劇烈煎熬、對自己的理智毫不留情的鞭策、對愛的需求以及同時又以苛刻的態度排斥愛,我傾向於相信,他的一生是極度不開心的。然而,臨終時他自己卻驚嘆那是「美妙」的 一生 !對我而言,這彷彿是一句玄妙而又令人莫名感動的說話。 (作者中譯)
留意:Malcolm 說的「極度不開心」("fiercely unhappy)與「美妙」("wonderful")沒有矛盾,極度不開心的一生,也可以是美妙的;「開心」指的是感覺,「美妙」則是價值判斷,只是對一般人而言,活得極度不開心的一生,就很難評價為美妙了。(至於如何的一生才算美妙,這是個複雜的問題,不能在這篇短文處理。)
Oates的短篇小說,故事內容簡單,寫一個女子平凡的一生。她從沒離開過家鄉小鎮尤維爾(Yewville,虛構的,美國沒有這地方),在本地的社區學院畢業後便結婚,與丈夫合夥賣了一間小書店,經營了幾十年,也生兒育女;丈夫去世後她繼續經營書店,還舉辦讀詩會,給本地詩人有機會公開朗誦作品,她免費提供咖啡及自己烘焙的曲奇餅和布朗尼。她私下還寫詩,從未發表過;在一次以女性詩作為主題的讀詩會,她鼓起勇氣朗誦了自己的作品,朋友、顧客和鄰居們都嘖嘖稱奇,驚奇她做了那麼多年的「隱蔽詩人」,並稱讚她的作品。她自己當然不奇怪,因為她從小就愛書、愛閱讀、愛寫作,還希望成為作家,成為詩人,希望有一天在書脊上看到自己的名字。她學業成績一直很好,可是,在決定她大學前途的公開試那天,她病倒了,是支氣管炎,頭暈、咳嗽、喉嚨痛;還有,考試之前那天晚上,她父母吵架,弄得她整夜睡不好,只睡了一兩個小時便要起來去考試。於是,她考試表現失準,結果得分平平,考不上心儀的頂尖學府。反觀她最好的朋友,平時成績及不上她,卻被康奈爾大學錄取了。就這樣,她好像便被決定了在小鎮過平凡的一生,不會在書脊上看到自己的名字。
然而,小說是這樣收結的:
出於自尊,也出於對你所擁有生活的滿足,你從不去想那走出尤維爾的另一人生。那個拿起筆來、以自信與才智全力迎戰考試的女孩;那個能夠保持鎮定的女孩;那個父母沒有爭吵、沒有在她人生中最重要清晨前一夜令她徹夜難眠的女孩;那個沒有喉嚨痛、沒有劇烈咳嗽的女孩。
你不耐煩地 搖了搖頭 ,其實也帶著一點快意地,別問我,這真是個愚蠢的問題。我當然是快樂的。我擁有我想要的一切。我的人生還缺少甚麼嗎?–– 一樣也沒有。(作者中譯)
最後幾句原文用斜體,其中有 "happy" 一字,我翻譯為「快樂」:"Of course I am happy. I have everything I want. What is missing from my life? ––not a thing." 為甚麼不譯為「開心」?因為「我擁有我想要的一切。我的人生還缺少甚麼嗎?– 一樣也沒有」是對自己一生的概括,反映的是一個整體看法,而不是表達感覺。「快樂」雖及不上「美妙」,但已是十分正面的評價。
另一方面,這篇小說充滿張力以及曖昧的描述,很多地方都可以有相反的解讀。她真的快樂嗎?她真的從不去想那走出尤維爾的另一人生嗎?難說,也許是真的,也許不是。只有她擺脫自欺、捫心自問,才有機會找到確切的答案。
這個故事還有另一種讀法。由於全篇用第二人稱 "You",可以理解為考試時事實上沒有生病、成為著名作家的「我」,在想像那個困在尤維爾的「你」,過了截然不同的人生;用「你」而不用「她」,拉近了距離,卻仍然是不同。最後斜體那幾句則是這個「我」說的,而她這樣說,同樣也許是真的,也許不是。
那麼,維根斯坦的臨終遺言是真話嗎?他有想像過他的平行人生嗎?我當然無從知曉。從第三者的角度看,我認為他的一生是wonderful的,但這裏重要的是他對自己一生的評價,不是其他人的評價。任何決心好好地過活的人,都應該想像臨終時會對自己一生如何評價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