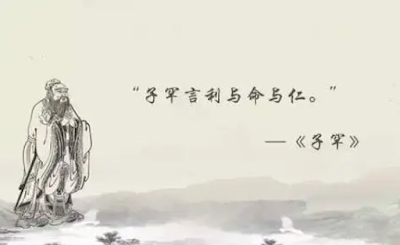王維詩有「晚年惟好靜,萬事不關心」(《酬張少府》)之句,後者我自問做不到,但確實是越來越好靜了。以前經常邀請朋友到我家聚會,或吃晚飯,或開派對,或看電影,或喝下午茶閒聊,一個月總有幾次,樂此不疲。然而,後來越來越少這樣做,近年幾乎沒有;最享受獨自在家,在書房讀書寫作,在廚房烹小鮮炒家常菜,過兩口子簡樸的生活。幾年前的疫情固然是一個因素,不過,與其說是疫情所致,不如說是因疫情之利而乘便,減少社交,配合好靜的心境。
問題是,我為何變得好靜?是年紀大了就自然如此嗎?看來不是,因為很多中老年人都喜歡熱鬧。對於自己為何變得好靜,本來沒有多想,但近日讀到周作人一封書信,忽有所悟,找到了解釋。那是周作人寫給孫伏園的,其中一段這樣寫:
我在濟南四天,講演了八次。範圍題目都由我自己選定,本來已是自由極了,但是想來想去總覺得沒有甚麼可講,勉強擬了幾個題目,都沒有十分把握,至於所講的話覺得不能句句確實,句句表現出真誠的氣分來,那是更不必說了。就是平常談話,也常覺得自己有些話是虛空的,不與心情切實相應,說出時便即知道,感到一種惡心的寂寞,好像是嘴裏嚐到了肥皂。(1924年6月10日)
說話虛空,不與心情切實相應,可稱為「虛應」。我發覺,原來我是厭倦了虛應,所以才好靜。社交應酬,現在對我來說,主要就是一個「倦」字,是心倦,而心倦是虛應帶來的。
從前也有很多虛應,為甚麼不覺心倦呢?也許是由於年輕力壯時精神向外,在不同方向擴展,虛應是無可避免的小支路;在大道上走得起勁,小支路便不會倦人了。中年以後,我的精神越來越向內,自察自省,要求說話行為都不虛耗自己,盡量活出完整真實的我;於是越來越不願意虛應,避不了的,便容易引起心倦的感覺。
這也能解釋我為何喜歡使用臉書。雖然我倦於虛應,但仍然喜歡表達自己的思想感情;在臉書上表達,不但可以真切地表達,而且不必虛應——不想回應的留言,可以索性不理會。
周作人那個「嘴裏嘗到了肥皂」的比喻真貼切。儘管我未嚐過肥皂,但相信口感和味道都是不好受的;虛應的說話,就算聞者感到「香氣」,說者可能比味同嚼蠟更難受,因為嚼蠟也許還可以同時訴苦,但嚼肥皂時卻要裝作很樂意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