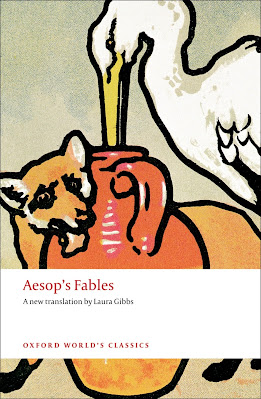最近讀了法國哲學家西蒙波娃(Simone de Beauvoir)的一本小書,友人鄭重推薦的,認為我會喜歡;他估計準確,我讀後確實激賞。本書寫的是西蒙波娃母親臨終的過程,寫得平實、細緻、深刻動人;探討的除了死亡、衰老、受苦、親情的糾結,還有醫療系統裏各方的關係。約一百頁,一個下午便讀完;讀後低迴思索,感慨良多。
我不懂法文,讀的是英譯,書名為 "A Very Easy Death"。法文原文書名是 "Une mort très douce",但 "douce" 不只是「容易」的意思,而兼有「溫柔」、「柔和」、「不帶痛苦」的含義;比起英文書名更傷感和更富反諷意味。中譯本(周桂音譯)書名是「一場極為安詳的死亡」,「安詳」也比 "easy" 的意思豐富。
此書無半分矯情,感人而不猛烈;看不到刻意鋪排的戲劇性,卻有極強的情感張力;絲毫沒有故作高深的「哲學腔」,但有哲學深度。給我的感覺是,應該寫的都寫了,並且寫得恰到好處,增之一分則太長,減之一分則太短 。我最欣賞的,是作者能以冷峻的筆觸,自然地透出令人感到真實的溫情,both detached and involved,而不覺突兀。
以下一段是我特別喜歡的,應該可以反映全書質素。手頭沒有中譯本,又不想從英譯再譯,最方便的是用 AI 翻譯法文原文;以下是 ChatGPT 的中譯,我對照過英譯,作了少許修改:
我不知道甚麼是信仰。但宗教是她生命的支柱,也是其實質:從她抽屜裏找到的文件證實了這一點。如果她只是把祈禱當作一種機械的喃喃自語,那麼數念珠對她來說不會比玩填字遊戲更累。她不祈禱這個事實,反而讓我確信,對她來說,祈禱是一種需要專注、思考和特定心境的操練。她知道自己應該對上帝說甚麼:「請治癒我。但願您的旨意得以實現:我接受死亡。」但她並未接受。在那真實的一刻,她不願說出違心之言,但她也不允許自己反抗。她選擇沉默:「上帝是仁慈的。」
「我不明白,」沃捷小姐驚訝地對我說,「你媽媽那麼虔誠,那麼篤信宗教,怎麼會這麼害怕死亡呢?」
她難道不知道,有些宗教聖人也是在尖叫與抽搐中死去的嗎?媽媽其實既不懼怕上帝,也不懼怕魔鬼:她只是害怕離開這個世界。我的外祖母臨終前清楚知道自己要走了,她愉快地說:「我要吃最後一顆水煮蛋,然後去找古斯塔夫。」她一向對生活沒甚麼熱情;八十四歲時,她已經悶悶地苟活著,死亡並不令她覺得不安或煩惱。我父親也表現得毫不遜色,他對我說:「叫你媽不要找神父來,我不想演戲。」他還清楚地交代了一些實際事務。破產又心灰意冷的他,對虛無的接受就如外祖母對天堂的接受那樣平靜。媽媽熱愛生命,就像我一樣;面對死亡時,她和我一樣懷有反抗的情感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