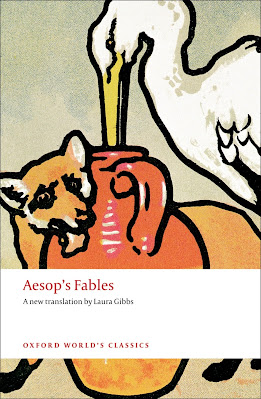1.
七月歐遊,差不多一整個月,前半和友人夫婦同乘遊輪,由荷蘭阿姆斯特丹出發,去了波蘭、瑞典、愛沙尼亞、芬蘭和丹麥;後半我倆參加旅遊團,遊了愛沙尼亞、拉脫維亞、立陶宛和波蘭。有兩個國家重疊了,但只有愛沙尼亞的塔林(Tallinn)是重遊。
1.1
我們乘坐的遊輪屬於 Celebrity Cruises,服務一流,營運安排(logistics)簡便流暢,食物質素亦佳,值得推薦。這不是我們第一次光顧
Celebrity Cruises,印象一向都好,這次尤其滿意。
1.2 後半參加的旅行團屬於 Gate 1 Travel,這是我們第五次光顧,喜歡他們彈性的安排,例如很多天的下午可以選擇自由時間(如參加他們安排的行程則要加費);我們通常選擇自己穿街過巷,到處走走。如果習慣走馬看花式、每天去很多地方的旅行團,Gate
1 Travel 便可能不適合你了。
1.3 遊輪每到一地,通常都有須要另付費的 shore excursion,以往我們會參加一些,但這次完全沒有參加,都是下船自己遊玩。我們在幾個大城市參加了
free walking tour,其實並非免費,因此又稱 tip-based walking tour,通常是一個導遊帶幾個到十幾個遊客,不用先付費,遊覽完畢後按導遊的表現(和自己的良心)付小費;導遊為了多掙些小費,都會很落力,講解豐富並力求生動有趣。所遊之處大多是有歷史意義的景點,全程步行,一般是兩小時到兩個半小時,每人付二十美元小費已合理,高興的當然可以多付。
2. 這次和友人夫婦同遊,乃一大樂趣;相處融洽,有談笑戲謔,也有嚴肅討論。我們兩三年前才開始熟一點,這次同遊,天天一起十多天,友誼加深了很多,大有相見恨晚之感。到了我們這把年紀還結識到好朋友,是非常難得的。
2.1 同遊的趣事不少,但特別值得寫出來的一件則是緊張刺激。那天在波蘭的格但斯克(Gdańsk)下船,遊了大半天,本來預了充裕的時間回來上船,但因一些事故,延遲了。到乘計程車回來時,時間已非常緊迫;其中涉及幾個決定,例如找出租車還是計程車、在哪裏找,只要其中一個決定錯了,我們便很可能趕不及上船。終於在上船時限前二十分鐘趕回,抹一把汗,頻呼幸運。遊輪絕不等人,要是遲了,便要自己想辦法趕往下一站,那是瑞典的維斯比(Visby)!
2.2 這次旅遊大小事務的安排,由訂船票開始,都由我老婆大人安排,事事妥貼,無微不至,我們稱她「隊長」,做坐享其成的大懶人「隊員」。
2.3 我們曾在多個城市玩 Segway (賽格威,港譯「攝位車」)遊覽,覺得很好玩,這次在哥本哈根也玩了。友人夫婦本來有點擔憂操控
Segway 可能不易,我們再三強調非常容易,試用五分鐘便可充分駕馭。他們開始時有點緊張,但真的不到五分鐘便控制自如,有人後來還玩 S 形花式 Segway 呢!
3. 愛沙尼亞、拉脫維亞、立陶宛合稱「波羅的海三國(Baltic States)」,雖各有不同,但相近之處更多,是我們這次歐遊最喜歡的國家。
3.1 波羅的海三國都可稱小國寡民:愛沙尼亞人口一百三十多萬,拉脫維亞一百八十多萬,立陶宛兩百八十多萬,加起來也沒有香港人口之多。由於人不多,就算在遊客區,也不擁擠,沒有巴黎、羅馬、東京等大城市的煩囂和壓迫感,遊覽時感到很自在。
3.2 三個國家的人都非常友善,例如駕車者見到行人想過馬路,即使不是斑馬線,也大多停下讓路;我見過一個遊客在車路上行走,沒留意背後有車,駕車者仍然很有耐性,沒有按喇叭催促,慢駛跟著,等到行人沒有擋住,才加速而去。
3.3 三個國家的風景都很美,在公路上坐車時不斷看到深淺不同的綠,層層疊疊,加上蔚藍的天和千變萬化的白雲,當真賞心悅目,令人心矌神怡。
3.4 在立陶宛街上見到不少美女,有些美得像模特兒或明星,這是在別的城市從所未見的。後來網友告訴我,波羅的海三國盛產女性模特兒,據說全球第一(https://3seaseurope.com/baltic-countries-female-models-estonia/)。那麼為何我在愛沙尼亞和拉脫維亞沒有見到很多呢?原因很簡單:因為我在立陶宛去的地方有較多本地人,在愛沙尼亞和拉脫維亞則不是。
4. 這篇遊記稱為「雜記」,還用了列點形式,就是因為所記之事零零碎碎。以下各點沒有任何關聯,只是我認為值得一記。
4.1 Gate 1 旅行團這次的導遊是個怪人,整日臉紅紅像喝醉酒(但其實不是),說話的語氣神態都有點不自然;雖然經常滿臉笑容,卻又會說話得罪顧客,例如他竟當面說一對團友是
"complainers",令他們大為不悅。此外,他的一些安排也不夠細心,引起混淆。然而,他的另一些做法卻很能取悅顧客。最特別的一次,是我們遊覽到導遊的家鄉時,他竟安排了一個驚喜,讓他已退休的父母帶同他的兩隻小狗來歡迎我們,並請我們吃(很好吃的)芝士和自己做的炸麵包,還有香檳和當地特產的烈酒。氣氛搞得極好,團友都很高興。
4.2 雖然我們對波蘭沒有特別好的印象,但我畢竟是蕭邦愛好者,參觀蕭邦博物館很有朝聖的意味;看到蕭邦自用的鋼琴完好地保留著,在館裏展覽,有一種莫名的感動(我在台灣故宮博物院看到蘇軾手書《前赤壁賦》時,也有同樣的感動)。
4.3 在華沙的另一次美好音樂經驗,是在 St. John's Cathedral 聽管風琴,尤其是聽到巴赫的名曲
Toccata and Fugue in D Minor,那種震撼,要在音響效果好、管風琴夠大的宏偉教堂才會經驗到。
4.4 據說有些歐洲人不是天天洗澡,我們在乘火車從華沙到格勒古夫(Kraków),車程兩個多小時,在車廂內就聞到不少人身上有難聞的氣味,也許是這個說法的佐證。
4.5 有些人有飛行恐懼症(aviophobia),這次我近距離見到一位。從阿姆斯特丹飛往塔林,只需兩小時左右,坐在我旁邊的年輕女士一坐下便顯得非常緊張。飛機一開動,我便留意到她一連串的動作:立即戴上太陽眼鏡,不但緊握座位的扶手,兩手同時交叉食指和中指(crossing
fingers);感到飛機離地升空時,她立即快速連環在胸前畫十字架,然後拿出手機,看著一些文字唸唸有詞,應該是在讀經文。兩小時的行程,她不時畫十字架和唸經文,太陽眼鏡一直戴著(這個真的不知道是甚麼意思),到飛機著陸才摘下。害怕到這個程度,肯定屬於
phobia。
4.6 最後一記參觀奧斯威辛(Auschwitz)集中營。這是二戰納粹德軍最大的集中營,超過一百萬人(主要是猶太人)慘死於此。這件人間最不義和令人悲憤的事,距今不過八十多年而已。參觀時不由自主地心情沉重,看到那堆滿一室被剪下的頭髮,另一滿室死者穿過的鞋子,實在震撼。甚麼「滿街都是聖人」,頓時顯得輕浮了。